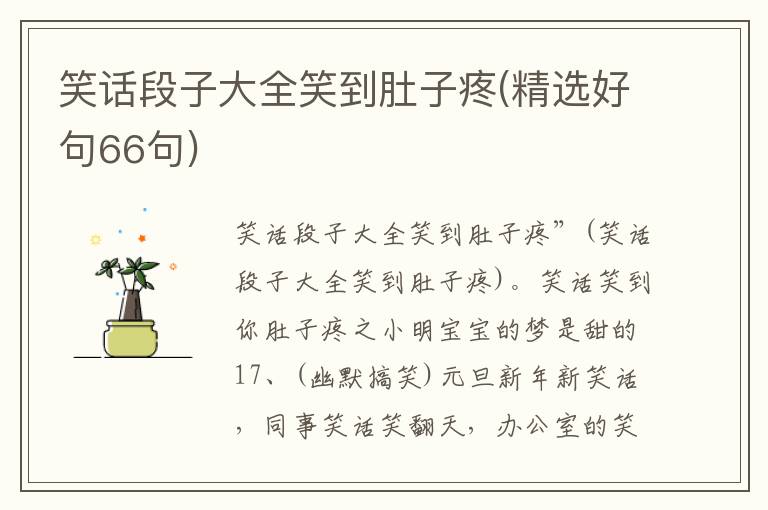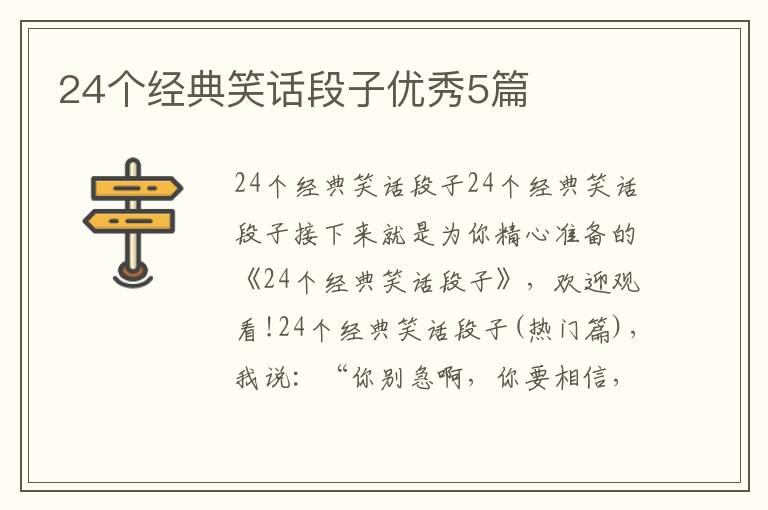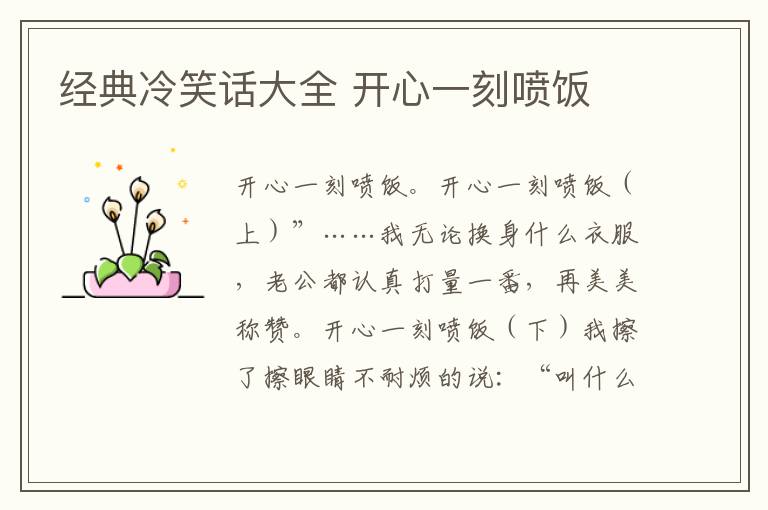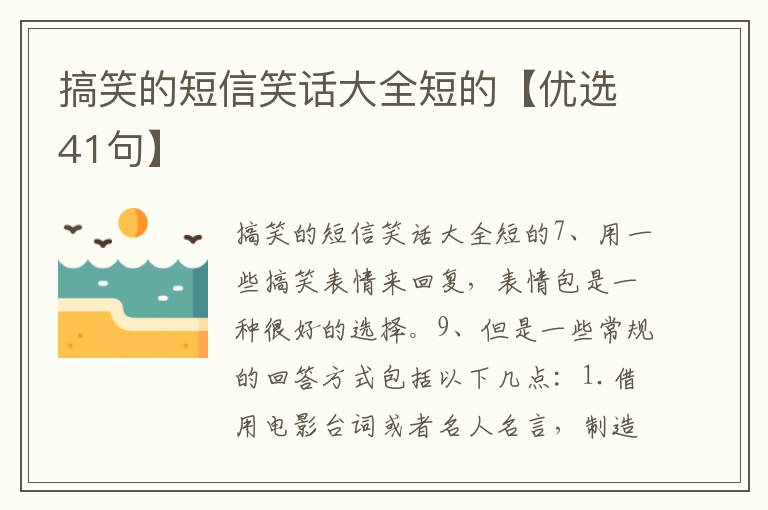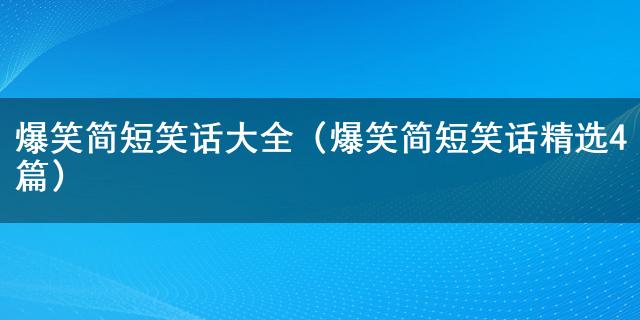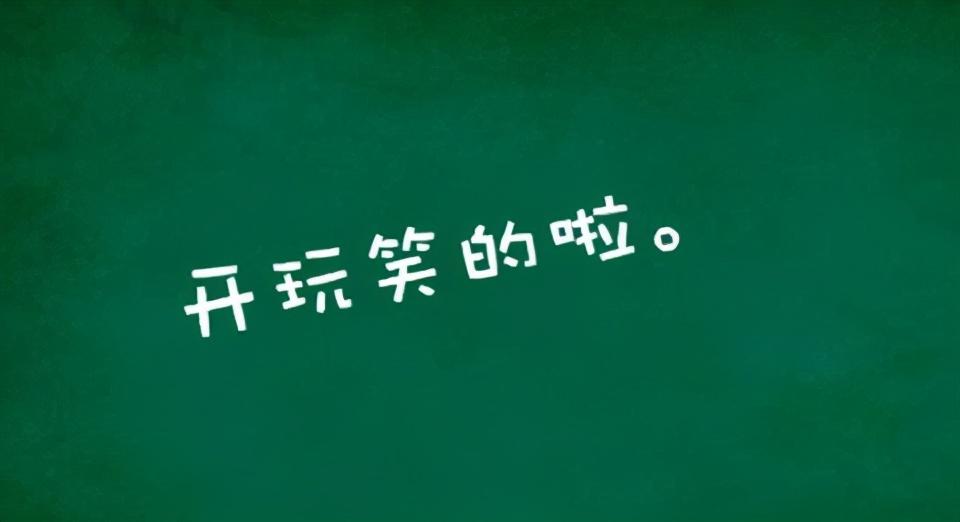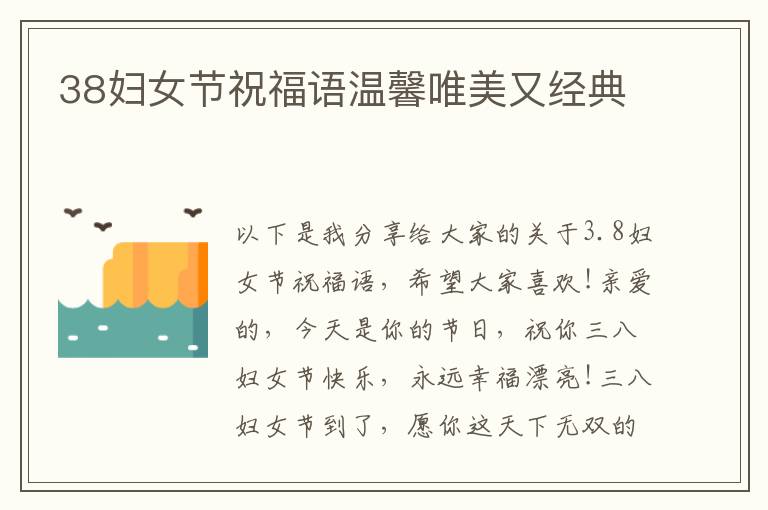獄中題壁譚嗣同名句

《獄中題壁》
望門投止思張儉,忍死須臾待杜根。
我自橫刀向天笑,去留肝膽兩昆侖。
自鴉片戰(zhàn)爭(zhēng)開始,中國(guó)進(jìn)入“三千年未有之變局”。自“開眼看世界第一人”林則徐開始,中國(guó)也被迫漸漸融入世界,在列強(qiáng)的凌辱下進(jìn)行艱難的現(xiàn)代化。林則徐翻譯《四洲志》,是為了解世界,李鴻章領(lǐng)導(dǎo)洋務(wù)運(yùn)動(dòng),是為器物層次上的現(xiàn)代化,而“公車上書”運(yùn)動(dòng)中凸顯出的學(xué)生領(lǐng)袖們則想在政治層面對(duì)中國(guó)的制度進(jìn)行改良。最終,經(jīng)過這些愛國(guó)舉子們的努力,年輕的皇帝被打動(dòng)。
清光緒二十四年(1898年),雄心勃勃的光緒皇帝頒布了“明定國(guó)是”詔書,宣布進(jìn)行變法。但是,僅僅百天,維新運(yùn)動(dòng)就失敗了,慈禧太后發(fā)動(dòng)政變,不但囚禁光緒皇帝,而且開始大肆搜捕和屠殺維新派人物。維新派的領(lǐng)導(dǎo)人康有為由上海逃往香港,梁?jiǎn)⒊步?jīng)天津逃往日本。
譚嗣同本也有機(jī)會(huì)逃走,可是,他卻堅(jiān)決不走,誓死要喚醒國(guó)人的覺醒。他說:“各國(guó)變法,無不從流血而成,今中國(guó)未聞?dòng)幸蜃兎ǘ餮撸藝?guó)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,請(qǐng)自嗣同始。”清廷抓捕了“戊戌六君子”楊深秀、楊銳、劉光第、林旭、康廣仁、譚嗣同六人,以“毋庸鞠訊”的幌子,急急忙忙地殺害了六君子。這首詩(shī)就是譚嗣同行刑前在獄中壁上所題。
張儉是東漢名仕。《后漢書·黨錮列傳》記載,東漢末年,中常侍侯覽仗著皇帝的恩寵,在山東老家和家人為非作歹,殘害百姓。張儉出于正義和蒼生的福祉,上書彈劾侯覽和其母親,請(qǐng)皇帝誅殺他們。但侯覽不僅截留了張儉的彈劾章表,還勾結(jié)其他人誣告張儉和同郡的24人“結(jié)黨”。
于是,朝廷發(fā)文書欲捉拿張儉。得知消息,張儉被迫逃跑,見有人家就去投宿(望門投宿之意)。這些人家,不管認(rèn)識(shí)或不認(rèn)識(shí)張儉,只要聽到他的名字,無不因?yàn)榫粗厮牡滦卸樟羲?jù)說,張儉所投靠的人家,被處以重刑的就有好幾十戶,有的人家族的親屬都被處死,這個(gè)地區(qū)的人口都一度蕭條。
當(dāng)張儉逃到了李篤家,負(fù)責(zé)追捕的毛欽帶人來查問。李篤對(duì)毛欽說:“張儉是天下的義士,大家都知道他沒有罪,即使張儉現(xiàn)在在我家,你忍心抓走他嗎?”毛欽聽了這番話,嘆息一聲就走了。最后,李篤把張儉送出關(guān)外,24年后,黨錮之禍解除后,他才回鄉(xiāng)里。
“望門投止思張儉”,應(yīng)該說是“思張儉之望門投止”,意思是想起了張儉逃亡時(shí)的匆忙和人們對(duì)他的尊敬來。作者為什么會(huì)想起張儉呢?聯(lián)系下句的典故或許就會(huì)有答案。杜根也是東漢名仕。杜根生活的年代,太后執(zhí)政,外戚專權(quán)。杜根認(rèn)為漢安帝已經(jīng)成人,理當(dāng)親自處理政務(wù),便和一些正直的大臣一起上書勸太后還政于安帝。
這極大激怒了太后,她讓人用白色袋子裝著杜根,要將其在大殿上活活打死。但是行刑的人都知道杜根是正直的人,佩服他的為人,行刑的時(shí)候沒有用力,打完就用車子把杜根迅速地運(yùn)出城去。后來,太后讓人來檢查,杜根就裝死,一連裝了三天,直到眼睛里生了蛆(忍死),人們都以為他死了,這才逃過一劫。
“望門投止思張儉,忍死須臾待杜根”兩句的關(guān)鍵在“思”、“待”二字上。張儉和杜根都是有名的義士,他們“望門投止”、“忍死須臾”的故事也天下共知。“思張儉”因?yàn)樗牡滦懈袆?dòng)世人,以致人們?yōu)榱耸樟羲麑幵缸约杭移迫送觯缚盗旱热颂油鰰r(shí)也有百姓愿意保護(hù)他們。
“待杜根”是因?yàn)椴粌H僅是杜根裝死逃過一劫,而是自己沒有像杜根那樣直接上書慈禧請(qǐng)其歸政于光緒皇帝,心中有愧。而這個(gè)“忍死須臾”也有對(duì)康梁等人的告誡,讓他們稍加忍耐,逃過這殺身之禍后繼續(xù)為國(guó)事奔走。
“我自橫刀向天笑”之“笑”,讓人想起很多關(guān)聯(lián)的笑。林則徐“我與山靈相對(duì)笑,滿頭晴雪共難消”,是無奈心情下的豁達(dá);李鴻章“笑指盧溝橋畔月,幾人從此到瀛洲”,是自信滿滿的慷慨;而“橫刀向天笑”,古之有者也許就只有文天祥的“人生自古誰(shuí)無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能與其相提并論吧。
關(guān)于“昆侖”,后來的學(xué)者有多種解釋,如梁?jiǎn)⒊J(rèn)為這里的“兩昆侖”指的是康有為和大刀王五二人;而符逸公認(rèn)為“兩昆侖”指的是“生也昆侖,死也昆侖”;也有人認(rèn)為“兩昆侖”指的是昆侖奴。其實(shí),也不必糾結(jié)于這些具體的解釋,不管“昆侖”為何意,這“我自橫刀向天笑,去留肝膽兩昆侖”之豪氣已經(jīng)不需其他解釋而感染到無數(shù)讀者。
從全詩(shī)來看,作者前兩句連用典故,意在對(duì)逃亡的“同志”予以勉勵(lì),意在指出變法終究會(huì)成功。后兩句則在直抒胸臆,以笑對(duì)死亡,這份豪情可驚天地,更泣鬼神。戰(zhàn)友梁?jiǎn)⒊谧珜懙摹蹲T嗣同傳》中寫道:“復(fù)生(譚嗣同)之行誼磊落,轟天撼地,人人共知,是以不論。”這首詩(shī)正是最有力的證據(jù)!
這位坦蕩的君子以自己的性命來喚醒民眾,其浩然正氣,足可敬也,絲毫不遜張儉、杜根!譚嗣同的夫人李閏在丈夫就義后,自號(hào)“臾生”,并作悼亡詩(shī)“已無壯志酬明主,剩有臾生泣后塵”來紀(jì)念亡夫,更讓人動(dòng)容。這讓我不由得想起林覺民的《與妻書》,更讓我想起古往今來無數(shù)為國(guó)家、為民族而犧牲的人。
當(dāng)年公孫杵白問程嬰:“立孤與死孰難?”程嬰曰:“死易,立孤難耳。”公孫杵白答曰:“趙氏先君遇子厚,子強(qiáng)為其難者,吾為其易者,請(qǐng)先死。”人們都贊程嬰救孤之大德大義,殊不知這“死易”有多不易!古往今來,有多少人為國(guó)而殉命?除了文山先生、譚嗣同、林覺民,我們又能記起誰(shuí)呢?這首如黃鐘大呂般的詩(shī)也許是響徹心扉的啟迪之聲。
怎樣評(píng)價(jià)譚嗣同
譚嗣同自幼好學(xué),胸懷大志,少年時(shí)就有很強(qiáng)的民族意識(shí)。大家知道他,大部分是因?yàn)樗摹拔易詸M刀向天笑,去留肝膽兩昆侖”。他之所以能說出句,一方面是因?yàn)樗袀b肝義膽,另一方面他是真的身手不凡。
譚嗣同不僅學(xué)兼中外,還對(duì)劍術(shù)、騎術(shù)等很感興趣。據(jù)說他曾以大刀王五、通臂猿胡七為師。他向胡七學(xué)過太極拳、形意拳、锏;向王五學(xué)習(xí)雙刀。譚嗣同曾對(duì)王五說:“處夷四侵,國(guó)事日非,好男兒當(dāng)以這三尺青鋒殺出一條新路”,王五當(dāng)即表示:“有用我處,當(dāng)誓死報(bào)效!”由此可見,譚嗣同的俠肝義膽,救國(guó)之心。
譚嗣同不僅對(duì)武術(shù)感興趣,還對(duì)武學(xué)很有研究,他曾經(jīng)寫過《劍經(jīng)衍葛》。這本書在戊戌變法失敗的時(shí)候散失,實(shí)在是可惜。在譚嗣同的文集中,也有兩處關(guān)于武術(shù)的:
單刀神者葛稚川(東晉煉丹家葛洪),譚復(fù)后以千有年。——《單刀銘并敘》
橫絕太空,高使天穹,矧伊崆峒。
蕤賓之鐵,蟻鼻有烈,服之有截。——《雙劍銘》
從這兩處關(guān)于武術(shù)的詩(shī)句中,不難看出一個(gè)狹義之士的胸襟與氣魄。
已故戲劇家歐陽(yáng)予倩的祖父曾是譚嗣同的老師,據(jù)他回憶,幼時(shí)曾見他“蹲在地上,叫兩個(gè)人握緊他的辮根,一翻身站了起來,而另兩個(gè)人則都摔了一跤”。看來譚嗣同確實(shí)身手不凡,令人心生敬佩。
譚嗣同的選擇最中也證實(shí)了他作為一個(gè)俠義之士的堅(jiān)守,用自己的生命喚起國(guó)民的覺醒,用自己的詩(shī)句鼓勵(lì)后來者不畏犧牲。改革的行進(jìn)不僅僅需要面臨災(zāi)難時(shí)的保留火種,更需要一種精神,一種振奮,這種精神甚至比刀槍棍棒更有力量。
譚嗣同的"去留肝膽兩昆侖",兩昆侖指的是什么
昆侖必須與去留相結(jié)合來論,這本來是一句詩(shī),分不開的一句詩(shī),很多人硬要分開單拿昆侖去想象,越想越偏,還是以詩(shī)言詩(shī)吧。去留,去就是走了的人,留就是留下的人。兩不是指兩個(gè),它也不是確切的數(shù),它是詩(shī)的一種意境。飛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銀河落九天,你能說就是三千尺九個(gè)天嗎,肯定不能說,它就是詩(shī)人綻放的爛漫想象。昆侖指巍巍昆侖山應(yīng)該沒有錯(cuò)。這下全詩(shī)指向就全出來了。昆侖不是指兩個(gè)昆侖,是指多個(gè)昆侖,那就是說留下的人都是昆侖,走了的人也都是昆侖。去留約束住了昆侖,昆侖也只能形容去留。歷史告訴我們,走了的和留下的不是一個(gè)人,是很多人,這很多人都是昆侖。為什么許多專家學(xué)者非說昆侖是指某個(gè)人,他們的說法不是沒錯(cuò)誤,他們的錯(cuò)誤是昆侖必須是一個(gè)高大的人,好比康有為,梁?jiǎn)⒊@種說法遠(yuǎn)遠(yuǎn)離開了譚嗣同的初心。再者專家學(xué)者對(duì)兩的古板認(rèn)識(shí)更是錯(cuò)上加錯(cuò),難道才高八斗的專家學(xué)者不知道兩不是指確切的數(shù),只是詩(shī)的意境,就是因?yàn)樗麄冎赖奶嗔耍炊咏恢溃@也是物極必反不由自已。多少年人們爭(zhēng)論來爭(zhēng)論去無有定論,現(xiàn)在一撥迷團(tuán)還原譚嗣同揮詩(shī)的心境。譚嗣同即將赴死,想起了與他一起變法的人們,有得走為上,有得來不及走,心中一酸揮筆寫下絕命詩(shī),緬懷那些留下來和去了的在變法過程中做過貢獻(xiàn)的人們。留下的灑血喚民心,去了的遍地播火種,他們都是巍巍昆侖。以譚嗣同的品德而論昆侖決不單指某個(gè)人,生死面前譚嗣同選擇赴義,其大公無私章顯的是品德的崇高,人們推崇譚嗣同也都是為了那從容赴死一剎那的道德感動(dòng)。這樣一個(gè)沒有自我忘記自已的人會(huì)說我就是一個(gè)昆侖嗎?不會(huì),他心系的是沒有來的及走的人。我更原把留下的昆侖送給譚嗣同,理由是,來的及走沒有走給人的肅然起敬,我又收回了這個(gè)念頭,理由是,這不是潭嗣同的初心。去了的人那個(gè)不是昆侖,都是在變法中奉獻(xiàn)的人,都配得起昆侖。詩(shī)的精采處在于,兩字在中間擔(dān)起去和留,去的也昆侖,留的也昆侖。最后說點(diǎn)不自量的話,以上可是獨(dú)家觀點(diǎn),翻遍書也找不到的推倒專家學(xué)者的宏論,也是多年?duì)幾h中完美的結(jié)論,頭條最好推薦一下,要不以后有好的也不給頭條了,說笑話的,我是一個(gè)淡泊的人。
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的死有什么意義嗎